夏日去信
作者/夏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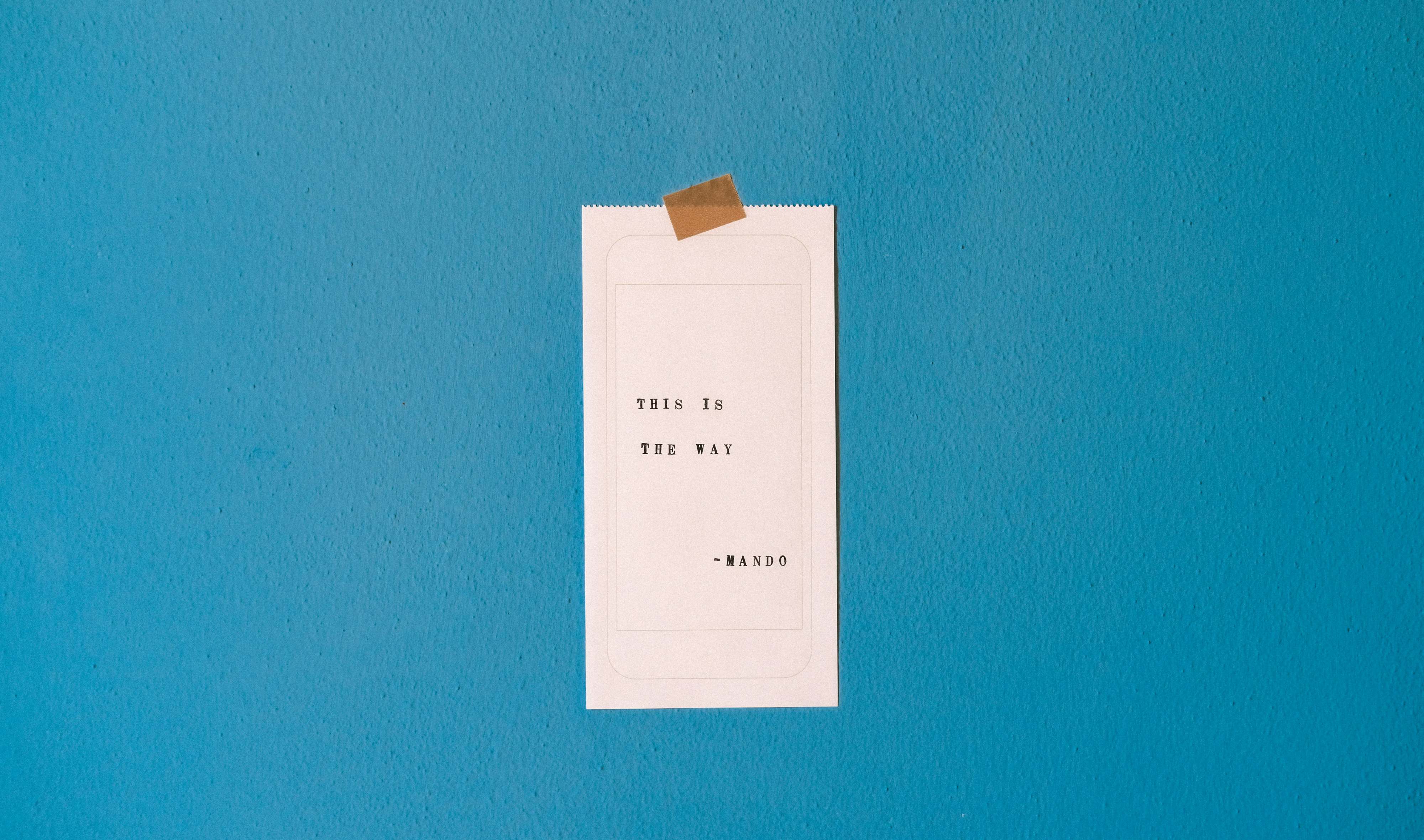
这就是我学字、写字的目的。回忆在叙述中得到复活,笔是侦探,找回、留档那些最关键的信息。
我在达里湖边看马群过河时,忽然觉得应该在这样的夏日午后里写信给你。
这是我第一次写你的名字。你姓李,在这个世界里急切行走着的,与你同姓的不在少数,比如我的母亲。你走后家更松散了些,这些年,轮到我身心受困。我像一只虫,以蚕食童年的快活光阴为生,活着活着竟将你也忘了。明明我真正失去的只有你。
一到夏夜,我就寂寞,所以我回到热闹的草原。
北京的夏夜挺温柔,但我最近还是频繁梦见小时候,我跟在你身后,等你把水从井里压到碗里端给我。月光斜进屋子,照着我一张单人床。是的,我至今孤单一人,虽然十几年前你还能在大坝上小跑时,我每日想的都是怎么摆脱羁绊。你眼中的我,定格在那个可以尽情浪费年华的小孩,尽管那时我的体魄已接近成人模样,五官与肢体都具备了发展至今的形状。
三四个月前,达里湖还在冬季。远处是望不到边的枯草,候鸟排成队伍准备归乡,万物栖息在大兴安岭山脉之下,等待遥远春日的真正抵达。克什克滕地区的严冬久久不开封,唯独达里湖深处的水流始终温吞,张开柔软的河床,为即将出生的婴儿留一块地。
两个月前,贡格尔河水冲下大兴安岭,形成道路,瓦氏雅罗鱼——你叫它们“华子鱼”——由此逆流涌上淡水区,在那孕育新的生命。大量渔船停泊在岸边,残留去年冬捕遗留的鱼腥和海藻遗迹,暗红色的“捕鱼船”三个字含义鲜明,游客们兴奋地等待鱼群上岸。
到了今天,我才想起你最后那几年的样子。你有张病床,比我的单人床再窄一些。医生宣布你今后的生活多数要在轮椅里,然后是床上。果然,从医院回家后,轮椅很快就不奏效,你女儿不知从哪弄来一张医院里常见的灰色病床。于是,清晨,鸟嘶鸣,摇臂将你升起,日落,鸟归巢,轴承再将你放下。你逐渐口齿不清,一天说不了几句话,身体与语言都困在那张床上。
我害怕夜晚。那么,在上千个安静的夜晚里,像你这样的人,在想些什么呢?
我现在也常常困在床铺里,因为一些都市人的常见病症无法入眠。我也病了,所以我理解你的那种寂寞了,却无法回到过去跟你分享这种理解。现代人耻于讲寂寞这个词,或许是因为如果把寂寞说出口,自我必定会有一部分折损在空气当中,自尊就少了一块。可此刻我手中只有寂寞这个词。
寂寞,寂寞。
日子偶尔有趣,多数寂寞,该怎么往下过呢。
好在夏日如期而至。人们说夏日总能发生奇迹。在大家都疲乏地午睡在旅店房间或蒙古包里时,我听见河边有小孩高声叫喊,他们奔跑着去追快要离岸的马群。童声划破夏日午后的烦闷之际,我想请你原谅我,在回忆我们的日子时,手里只剩下裂镜般虚实难分的碎片。
毕竟我也已经老了,许多个夏日已经一晃而过。
五年前,我从墨尔本毕业回国找工作时,你已躺在喀喇沁旗的土地里,那片土地是我诞生和长大的地方。母亲却说打算把你接回你的老家。我才知道,我的故乡,原来不是你的故乡?那时,我对你一无所知,只是大概明白,生于战乱年代的人没有不离乡的。你年少时,从克什克腾旗辗转颠簸到喀喇沁旗,从此在那生活大半辈子。你的母亲留在家乡,父亲不知所踪。
七十多年过去,少年终要回家。你将回到克什克腾旗,葬在你母亲身侧。离家后迷失在人海的日子总是漫长,回家的路却很快。
也是一个七月,雨夜,通往克什克腾旗的轿车里,母亲坐在我左侧驾驶。澳洲的驾驶位在右侧,我不时觉得母亲应该往相反的方向使力,这样的陌生感给了我一种超然,让我在送你回家的路上,像在旅行一般只看风景。汽车尾气留在榆树林、灌木丛,以及偶尔贴着高速路踱过的羊群之中,我忽然想起来,你连自家轿车也没坐过,你开始需要卧床生活时,我们家庭里还没有谁能买一部轿车。
我是内蒙人,有个蒙古名字,我喝咸奶茶,听德德玛的蒙古歌长大,身份证上的每个字都有蒙文标注。但我没去过草原,也不会说蒙语。那么生于草原的你是会说一点蒙语的吗?——那样的你对于我来说,真像一个无关之人。
不同于省际路、城际路、高铁身下的平整的路、以及国际航线上空如梦的晴云大道,去往你家的那条路,坑坑洼洼的。我们在泥土上留下车辙。
我问母亲,手续是否都办好了?
其实这些年来,你女儿做事变得仔细妥当,一改她婚前像个男孩的个性。我知道她不少故事:小时候领着一班女孩抗议寻事被学校开除、婚后时常在煎炒时把烫伤手指、在合同上轻易画押、或者独自坐公交去医院做小手术,不肯麻药,痛晕在诊室里……这样年复一年地活下来——那是在你的呵护下,一个女孩成长至一个女人的过程。
由于接受了你的死亡,也使她的成长彻底完满了。你没有那个年代里惯有的重男轻女的风格,一位妻子和两个女儿,这是你对自己人生的全部嘱托,并尽全力经营家庭。你在畜牧学院上学时爱读俄国文学,最喜欢那句“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,然后是正直的,然后——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。”
雨刷器减慢速度,母亲右手拉住我,回答似地使劲儿攥了攥。
在县城小旅馆住下的第二日清晨,夏鸟叫得旺,蝉鸣包围了树林。早饭是吊炉烧饼、芝麻萝卜咸菜、咸奶茶泡炒米,五元一位。这里离克什克腾草原不太远了,许多外地游客赶在七八月来看草,这是草最好的时候。
六点钟,我和母亲站在山坡上,各自在心里对你讲话。你就长眠在这吧。一座座小丘陵在你身旁随机散落。大山坡的另一个侧面,还有一家人在烧纸。我们远看着对方,通过缕缕上升的青烟就算认识了。
烟味使我回想起来,幼时我就站在一个这样的山坡上,等姥姥叫我和表姐回家吃饭。灶膛里烈火滚滚,拱起一口硕大的铁锅,你蹲在灶膛口往里添柴火。秋天我们从自家地里摘下玉米、扁豆角,吃院子中央那棵树结的杏;冬天我们炖腌酸菜,冻豆腐,唆冻梨,啃国光苹果。这样简单的食物反复吃,将我喂成这样的人。
这么想着,一阵大风忽起,把带着火星的纸吹得到处都是。两队人一起扑了好一会,火才灭了。在火遗留的味道中,我想,不久后你还会在这里吗?我感觉脚下的土地在缓慢地旋转。地壳在每个夜晚移步一点,今天不是昨天,明天也不会是今天了。那天我的手指尖被烧出个火泡,回到北京上班后,还行动不便了好几天。
不过,那座山因为你的存在具有了某种美感。后来,每当我坐着火车看见、或只是在电子地图上划过这种土黄色的山丘时,心头都会产生一种亲切。
我没听过你讲什么大道理,你就是在土地上过生活。这是你教了你女儿,你女儿又教了我的:做一个不伤害别人、不悔恨的人。至于其余的错误,犯了就犯了。
比如二零一二年你去世那天,我还悠哉地去了墨尔本一家网红汉堡店吃汉堡。在我得知你走了的消息时,家里所有人早就换了一种身份——他们不必再照料你了,从病房、葬礼退回到个体的生活。只有我失去了这次预习死亡的机会,错过与你当面的道别。
直到今天看见那群过河的马、尖叫嬉戏的孩子,以及游客们在闷热的夏日午后里休息,沉睡。我觉得活下来真好。
老房子卖出之前我回去过一次,屋子里只剩那张淡灰色的病床没人要。有一次,你歪靠在床头,怎么使劲也捏不起碗里一块肉。你愤怒地打翻姥姥手里的碗,把桌上的盘子勺子扫到地上,将全家人骂了个遍。
想到这,我觉得挺好笑。上一次你大骂人,骂的还是我。那是我五岁时,有一回跟着镇子里的小男孩去东边看“大井”。你和姥姥急得流汗,跑遍了分叉的街巷。找到我时,我们几个小孩正一起趴在井口往下看,你们吓得够呛。姥姥哭着抱我,你则气得大骂我一顿,罚我面壁思过,然后好几天都没跟我讲话。那是你唯一一次责罚我。现在,即使我消失个两三天,也没有人去找我了。
大黄狗病逝那年,父母把我接回城里准备上小学,我都不记得你是因为大黄狗,还是因为我而哭了?你性格孤僻内省,不爱发脾气,更别提跟谁急眼,所以那天清晨在长途汽车站,你的眼眶红得像只兔子,太阳照着耳朵也红。至今你再来我梦里时,你的耳朵还是红的,毛细血管清晰可见。
我十二岁那年,你和姥姥进了城。你心梗病发,虽然只是有点口斜眼歪了,但生活仍能自理。我们常下象棋,有一次我悔棋,你气得一下子掀翻棋盘,棋子掉了一地。只是悔棋嘛,姥姥要你跟我道歉,你“咣”地摔门,一头躲进卧室。第二天一大早,你去大坝上晨跑,回来把我最爱吃的奶油味爆米花放在餐桌上。
一开始,你还可以快速地走,担任了接送我上下学的职责,你一丝不苟地领着我沿着同一条小路,保护我走过几个春夏秋冬。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,开运动会时,你偷偷守在校门口外,等着看我跑接力赛,你不知道的是,我透过校门口的栏杆看见你在门外等我了。那一双搜寻我身影的眼睛,让我想起二十年前你跑到井边找我的眼神。
那是我们最后的美好时光。二十年前,城市的清晨已经喧嚣,早上,窗外传来鸟叫和车流催促的喇叭声,邻居小孩“咚,咚”地拍着篮球上学。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吃早饭,牛奶箱里的“每日鲜奶”,你和我一人一瓶。我在班级里交了好朋友,每天都盼望赶快喝完牛奶上学跟她见面。那时,我们的家庭还十分完整,我们一老一小深受照料,都像小孩,不过是你往一头走,我往另一头走了。
只记得你摔了一跤,从医院回来后,就整日坐在椅子上。我每日上学,嗅着新世界的味道,难以一一关怀你的每况愈下。也许就是在我深陷人生中初次暗恋的日子里,你的普通椅子换成了轮椅的吧。那时我还不知道人生是趟单程旅行,身体的零件,一旦一个出现问题,就会一件接一件地出现问题。
后来,在我准备留学材料期间,你因为神经不受控制,开始常常忍不住大笑。我和表姐睡午觉,要你当闹钟,叫我们起床。一到时间,你就对着卧室喊个没完:“起来背英语!快起来背英语!”我跟表姐一边困得不想起,一边被你士兵喊“前进”般的口号给逗得不行,一听我们笑了,你也龇牙咧嘴笑起来,露出那两颗颜色很突出的后补的假牙。
那种不受控制的笑,那种喊叫,从你的胸腔里涌出时,你正在怎样感受这个世界呢?我的忽视、我的错过,使我没能做到你的教养——最终还是伤害到了别人、也让自己悔恨了很久。
六千五百万年前,欧亚板块与太平洋板块不停碰撞,由此形成了大兴安岭山脉。那是你的来处。你是历史中迅速出生又湮灭的一只蜉蝣。你是我母亲的父亲。可是,谁又是你的父亲呢?
回想起来,也许你一直坚持的那种教养,正是要打点好自己,去期盼一次与你父亲的见面吧。
你父亲早年逃到南方,战争落幕后回来寻你。他先是去了克什克腾,打听你的消息,然后辗转来到喀喇沁旗。那时表姐已经出生了,他没想到竟然能看到自己的曾孙。夜晚,你们坐在院子里,父子二人沉默不语。你父亲只是卷旱烟、抽旱烟,一根接一根,想把那幅四代同堂的画面记在心里。他觉得你把家庭和事业都看顾得很好。住了一个月左右,他就走了,此后又是杳无讯息,再也不复相见。
你多年来认真做事的风格、你整洁的生活习惯,以及你谨记在心的“正直、善良、永不相忘”,都是在等待那一个月的相处吧?即便不说话,也能够理解彼此的心意,体会彼此的痛苦。在那个只有月光和榆树林作为夜晚的声响的九十年代村镇,最清晰的话语莫过于身体的陪伴。
那个年代,离散的确是常事。人们因战事而动荡,纷纷跳入自己的河流。可是最后,我们所有人,还是得汇入同一片土地,随着暴雨、大雪的水分沿着地壳裂开的地方,漂游在永恒的时间里。
下午三点,蝉鸣得厉害。马群已经过了河,小孩子们累得走回餐室去吃冰镇西瓜和酸奶冰淇淋了。写到这里我才明白,这就是我学字、写字的目的。回忆在叙述中得到复活,笔是侦探,找回、留档那些最关键的信息。
责任编辑:梅不谈
